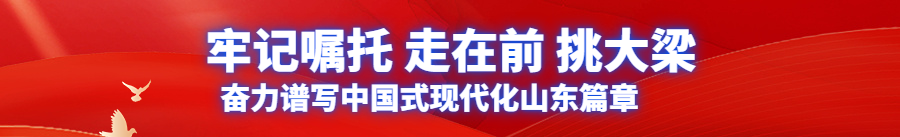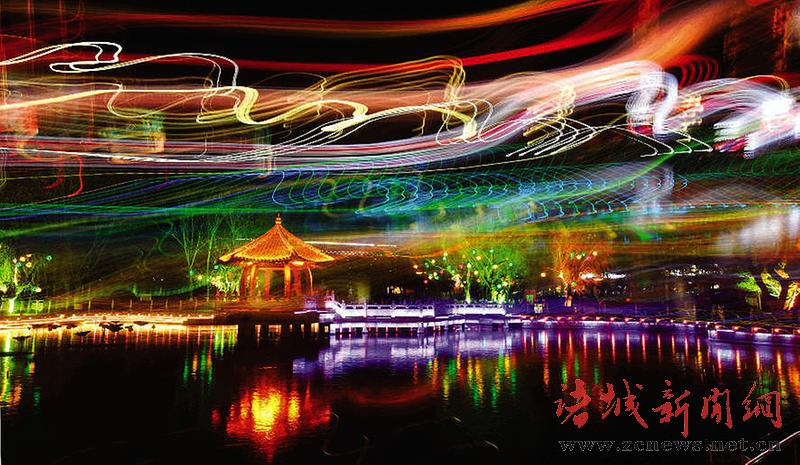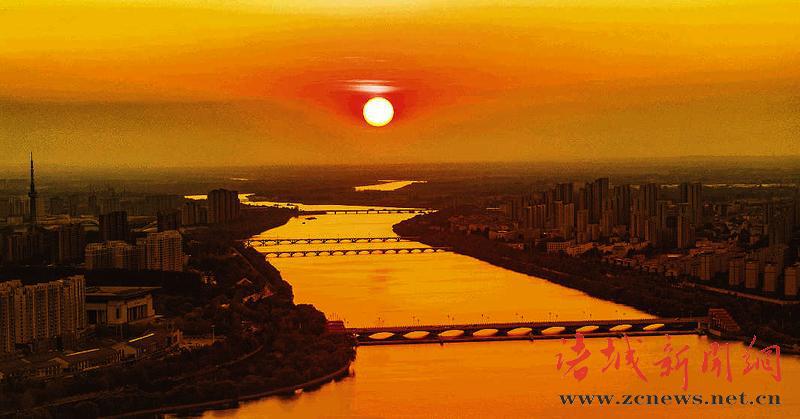曾经,我误会了一座山。
泰山,也只是在杜甫的远望下“阴阳割昏晓”。一座不及马耳山高的山,竟明目张胆地称“障日山”,真是狂妄至极。我心里满是疑惑。后来想到,山就是山,都是人冠于它名号,至于什么名号,山说了也不算,它就安安静静地做它的山。这样想的时候,心里也就有些释然了。
大概爱屋及乌。因为一个人亲切地称之为“小峨眉”,这让我既困惑又向往。直到我走近了它,触摸着它,感受着它,了解了它,心里油然滋生的是敬畏之心与欢喜之情。

景区介绍上说“以山高障日而得名”。我询问山根下屋村的耄耋老人,一个说,下午太阳早早地就落到山那边去了,可不就是障日嘛。一个说,山上有时云雾很重,把山严实地裹起来,太阳都露不出脸来,当然就叫障日山了。看来,“障日”得的确有理。
坐在“东坡泉”畔的平石上,一时间觉得不太真实。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奢侈了?每天忙忙碌碌,成了时间的奴隶,今日难得放纵,暂将一切繁杂烦心事抛诸脑后,心归山水,静享自然之趣。清风拂面,群山披翠。凝望久了,感觉心里也绿意盎然,如水洗尘。
穿越岁月的朝风暮雨,遥想当年,苏子从杭州调往密州,犹如从繁华天堂跌落凋敝之邦,心理落差不亚于黄果树瀑布。酒醒咨嗟,孤寂落寞如风袭来。灭蝗捕盗治旱教化民众等事务填满了时间的空隙,哪有闲暇吟风弄月?这是庸夫俗人的格调。苏子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俗人,他热爱生活,懂得享受生活。政务之余,品山读水,意趣无穷。正如他在《超然台记》所言:“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他喜游名山。障日山很幸运地入了他的慧眼。那些活了亿万岁的山岩巨石熟悉他的曳杖声和爽朗的笑声。丽日风清之时,或淡烟疏雨之际,三五好友,徜徉山林,流连泉畔,松花酿酒,山泉煮茶,流水曲觞,诵诗作赋,酬唱和答,文人该有的样子。百鸟和鸣,蓝天白云,抚慰了多少疲惫孤独的心灵。障日障日,反复咀嚼,是否会让人心生不悦?苏子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正心心念念着“何日遣冯唐”呢,罢罢,干脆改一下吧,“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听听,“小峨眉”,多么秀丽可爱!峨眉,峨眉,哦,那是苏子家乡的山啊。游子浮云,何日是归程?“此心安处是吾乡”,那卖油郎之妇竟有此等见识!有“小峨眉”相伴,就作身在故乡吧……超然世外,那是一种能力。我等俗人万不及一。
“石——门——爸爸,快来看,这里写着石——门。”小男孩声音洪亮,像身边清越的泉流。年轻的爸爸应声上前。

我拉回思绪的野缰。
路北山壁斜出巨石,虽坑凹斑驳,却是块整石。石门与山壁相连处有道裂缝,是谓门缝,这意味着门是可以开合的。可这石门与山一体,纵有千斤臂力,纵是二十级台风,也难动它丝毫。这石门有什么机关吗?敲敲打打,这里触触,那里摸摸,眼如探照灯,也没发现什么门道。人说“大道至简,大道无门”,因为山路狭窄崎岖多石,造化就弄一道石门吗?或者,打开石门就是通天大道了?或许仅仅是状似?山不言,石门不语,只能任人天马行空了。
木鱼石,又是一处神奇的石壁。相比“石鼓”的另一种说法,我更喜欢“木鱼石”。试想,深山古刹,老树虬枝,曲径通幽,空翠湿衣,木鱼声声,穿云而来,何等的空灵幽静。捡起脚下的石子,在石壁上随意敲打,铿铿锵锵,叮叮咚咚,空谷回响。支棱起耳朵,谛听天籁之音。一时间,无数只手,无数块石头,错错落落地忙碌着,一曲交响乐在山谷飘荡。 沉郁的心情早一扫而光。
忽然想到石鼓空心,那么石壁内是有空隙的,或许是一条空道。联想到前面的石门,莫非打开石门,就通向这里的空道,然后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非人间?里面藏着武林秘籍吧,藏着干将莫邪剑吧,有皓首老者在修仙炼道吧,是藏宝洞吧……我这样跟同伴说的时候,旁边一戴眼镜男子笑道:“看来那些年的武侠小说没少看。”我没有胡思乱想,是这山石本就神奇。
和着淙淙的流水,《高山流水》的曲子直抵心灵。虽是应景,也给这座朴素的山平添了些许高雅。想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绝唱,想起岳飞“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惆怅,知音难觅,亘古同心。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妹妹很惊讶,哪来的琴声?哪里弹琴?循声去找。她弯着腰,探着头,绕过乱石,在野草丛里逡巡。过了一会儿,她坐下了,神情凝重,似在谛听。她一定是探到答案了。她身后的岩石壁立如巨大平台,是依山面水抚琴的好所在。石壁成条形凹凸排列,宛若琴键。正中镌刻着“抚琴台”三个红色大字。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长发如瀑、衣袂飘飘的清丽女子,一双纤纤玉手,正在琴上轻拢慢捻。
一会儿,妹妹满意地回来了。银丝暗生的人了,还活泼得像身边蹦蹦跳跳的溪水,好奇心不亚于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小孩子。这是一种不老的少年心态吧。这点很令我感佩。忽然想到,多年的姊妹堪比知音啊。听曲勾起的怅然烟逝风中。

特意走木栈道,是为了看看白云寺。
白云寺,名字好。“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很美。文人墨客“早晚离尘事,谈空向野僧”“行吟出树下,云在意倶闲”,很惬意……我开始胡思乱想了。现今的白云寺,只剩下遗迹,布局历历可见,古井、钟楼、大殿、碑石……灶台都还保留着。听山下的老人说,曾经有三大寺:白云寺、法云寺、祥云寺,寺寺相连,足见当年的佛事规模之大,香火之盛。慈悲为怀,教人向善,信仰,是一种力量。
遗迹犹在,何日复活?
废墟中低矮的石墙基上有一粗大的树墩,大约有一人合抱。不用想那是棵怎样的大树,它经历了些什么,只这树墩就足以让人敬畏了。树墩上又生出了一根纤细的枝条,枝条上生出了几片柔嫩的绿叶,在山风里摇曳。这是生命的延续,是生命的宣言。几乎沿途中的山石峭壁上都能看见顽强绿着的生命,它们在绝处求生存,让人震撼。在“木鱼石”处,一位年轻的父亲,曾指着石壁上的小树,启发儿子“立根原在破岩中”那首诗的背诵。我赞赏那位父亲,这种现场引导,能让孩子真切地体会什么是艰难,什么是顽强的生命。
庙址西边空旷处有一株大树,叫不上名字。这树与山中的所有树木一样,没有呼吸到废气,没有遭受各种污染,洗过一样,叶片鲜绿、油亮。低处的树枝上系满了红布条,像垂下的艳红的花朵。这是一棵有灵性的树。它背负着多少虔诚的愿望啊。心诚则灵,但愿种种美好的愿望都能如期盛开。
我观望着那棵树,醉心着她的美。我没有许愿,因为不习惯,还因为我想起了看过的一个小故事:观音菩萨跪拜观音像,求人不如求已。
白云寺像是个中转站,许多游客在这里休息。有位年轻妈妈累得坐在地上不想起来,喊着爬不动了,不想爬了。小孩子硬是把她拉起来,拖着她继续往上爬。有四位大妈,是一起来的,年龄最小的也七十三了。她们说来都来了,不爬到山顶等于白来。在我累得气还没喘匀时,她们又起身了,眼见着几顶花色遮阳帽消失在绿树丛中。
见我在犹豫,妹说还差那几步了?来了就得上去看看,走。
“那几步”说得轻巧,爬起来还真不容易。有些路段须得手脚并用,分外留神。

走走停停,前瞻后顾,一步一景,大饱眼福。
神龟探海。其形酷肖。你的故乡是东海。何故淹留在此?亿万年了,你遥望故乡,望眼欲穿。悲苦心情,让文字也摇头叹息。
金蟾望月。从低处侧望,蟾,最形象的比喻。一个浪漫的神话故事。嫦娥移情别恋,而你痴心不改。亿万年的风霜雨雪,亿万年的沧海桑田,你的痴情可曾减半分?守望,是一种等待,一种希望,也是一种幸福。地不老,天不荒,你会一直守望下去。
栖云谷。充满了诗意。远望山顶下西北边,一道大沟,沟壁上一道道沟壑,很幽深。那些终日流浪的云,在此歇脚栖息,感受宾至如归的温暖。想象白云出屾或彩云荟萃,浩浩荡荡,何其壮观。
离山顶不远,有两棵松,很突兀。松不高,也不老,一棵身形挺拔,一棵身姿婀娜,相距咫尺,枝叶相牵。似在望日,似在观海,或是聆听山林涛声,或如相拥恋人喁喁低语。“情侣树”,这种叫法很好,恰称人意。想起舒婷《致橡树》中的句子:“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一对对男女在树前拍照。让青松作证,愿他们比翼连枝,生死契阔,永不相负。
山风浩大,站在巨石上摇摇晃晃。小心地挪步,那些“到此一游”被踩在脚下,那大片的刻字不易辨认。小心地观望,因为此山是由火山喷发熔岩堆积而成,又经过亿万年流水和风化又兼地理位置特殊,一只只巨蟾,一只只神龟,都以奔跑和翘首的姿态朝向东南——那是海的方向。那些姿态,仿佛在一瞬间被凝固成了永恒。
这是障日山独有的奇观。
到处可见页岩重叠堆积或错落,像打开的书本或厚重的书籍。这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事实面前,让人不得不叹服大自然的伟大神力。“山高我为峰”的狂言还未出口,早被自然的伟大神力击得灰飞烟灭。人,在大自然面前渺小如尘。
无限风光在险峰。四下眺望,青山层叠,绿野红瓦,水库如镜……虽隔遥远,也能感受到一排排大风车的慢条斯理。
目力所及,皆是风景,不登上山顶,绝无此眼福。
那四位大妈早已登顶。她们不惧风大,在最高石上或立或坐,拍照拍视频,存下美好记忆。
途中遇到的那几位望峰却步者,若看到这些老胳膊老腿在山顶悠游自在,该有些感慨吧。
曾听擦肩而过的一位大妈跟同伴说“这山上的都是宝”。此言不虚。一位手戴金镯项挂金链的大妈,提了大半篮子荆条叶芽,说炒干了当茶喝,是上等的中药材,村里人都知道,不少人来采。还听说,小孩受了惊吓,采七个荆条芽煮水喝,立竿见效。还遇到两名五六十岁的妇女在挖一种野菜,细长的叶片,鸽子蛋大的球根。问时,说叫“地刀子”(只是取其音),将根洗净捣碎拌上白醋,可以治什么病。路边草丛里时见山菜,山顶上更多。不少游客边爬山,边采山菜,一举两得。妹更是乐此不疲,她除了采山菜,还挖一种叫“板芡”的菜(我们小时候叫“六角子嘴”),可蘸酱生吃,可炒鸡蛋,可馇小豆腐,据说也是很好的中药。那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就无法罗列了。

今天周末,人多。扶老携幼,前呼后应。小姑娘喊着爸爸和弟弟,提醒别走右边,太危险;小男孩蹲下身,要背着妹妹上山。一位百岁老太太,在家人陪护下,拄着手杖,也来耍山。面容是沧桑沉淀后的慈祥与安恬。在木鱼石处,她拿着石头敲打的样子像孩子似的纯真。而我,弟弟替我挎着包,妹妹给我背着水壶,我赤手前进,紧要处妹妹还要搀扶我一把。亲情如温暖的春风,在山中荡漾,那些山花也笑得格外灿烂。
小女孩们采花拈草,快乐得像翩翩起舞的蝴蝶。小男孩们穿石越涧,像敏捷灵活的小猴子。年轻的姑娘小伙子,身穿薄衫,脸庞红润,上山下山,如履平地。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两个鬓染霜花的男子,牵藤拽石地爬上一处高耸的石块,振臂高呼,一股不服老的豪气直冲云霄。山间充满了朝气与活力。
快节奏的生活里,大多数人为物质奴役,双足像上足了劲的发条停不下来,精神日益焦虑。有时候,就需要慢下来。爬山,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疗愈。身在山中,过滤负面情绪,把焦虑、忧伤、愤懑、意难平……统统交给风去处理。慢下来,譬如牵着蜗牛去旅行,才会发现那些瞬间的美,并且美得不可收拾。二月兰、蒲公英、新移栽的映山红,叫不上名字的野花,没有一朵花是丑陋的。马尾松、柞树、枰柳、松柏、桲椤、皂荚树……没有一棵树不风姿独特。枯草里钻出的嫩芽,清新亮眼。那些紧紧拥抱巨石的青藤,让人想起海枯石烂之类的誓言。还有那香甜的洋槐花,一串一串,丁丁当当挂满了树。那一片白雪似的山楂花,仿佛转眼便是满树圆嘟嘟红通通的山楂……一只流连花丛的黑蝴蝶,也会让浮躁的心静下来。
百丈崖、红崖古战场、拴马桩、白云洞、水帘洞等景点,都没来得及涉足。并不觉得遗憾,就像坦然接受不完美的人生一样。
回到山坳口处,远望山下,还一片明亮,料想太阳还很高,而山这边明显地暗下来了,不见了一点树影。的确,山高障日。
每一次登山,都会增加一次人生的历练、修行与感悟。其实,登山如人生:目标在远方,答案在脚下,而意义在途中。登顶,只需要坚持一点,那就是走一步,再走一步。
再次望向离山门不远处的东坡书院,依旧大门紧闭。白墙上咏障日峰的诗句依稀可见。见与不见,“小峨眉”就在那里。
除了《障日峰》,苏子调离十年后再过密州,写下了《次韵徐积》:“海山入梦方东去,风雨留人得暂陪。若说峨眉眼前是,故乡何处不堪回。”表达了对密州的眷恋之情。
东坡喜爱“小峨眉”,我亦爱之。那些精美的诗文会像这障日山一样,永远不朽。
宋代诗人杨万里说,“远山不见我,而我见远山”。我们还会再来。
作者:孙晋芳
1 条记录 1/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