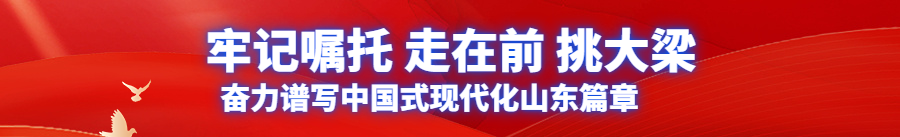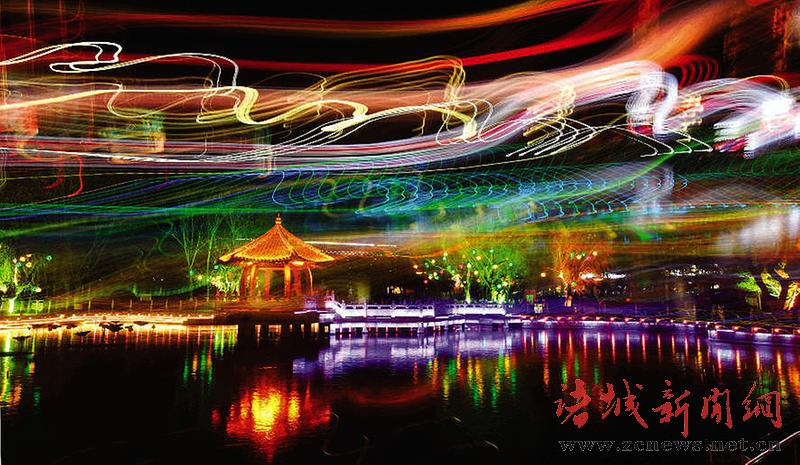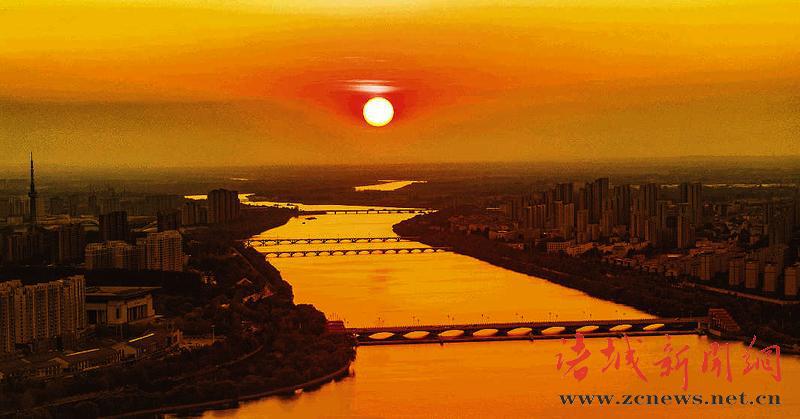“琅县”二字,虽仅寥寥,却如金石掷地,回响千年。它不仅与《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遥相呼应,更以确凿无疑的实物证据,印证了秦始皇在山东半岛设立琅琊郡县的历史事实。秦并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琊郡”赫然在列,其郡治即为琅琊县。
秦始皇在位期间五次出巡,有三次来到琅琊。秦始皇首次东巡时“大乐之,留三月”,更在此修筑巍峨壮丽的琅琊台,足见其对这片东海之滨的钟情与倚重。秦始皇何以如此垂青琅琊?此地究竟蕴藏着这位千古一帝怎样的战略考量与心志?“琅县”铭文的浮现,恰似一把钥匙,开启了对那段历史深层逻辑的探寻之门。
古井中出土两件“重量级”文物
营前村墓地(遗址)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营前村北800米处,遗址地势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北侧紧邻琅琊古墓,南侧紧邻营前遗址。该遗址位于战国、秦汉琅琊邑城东南部,在琅琊城到琅琊台的必经之路上,年代跨战国、秦、汉。
今年3月至5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西海岸新区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各类遗迹51处,包括墓葬13座、水井6口、灰沟9条等,出土铜印章、玉具剑、陶罐等各类珍贵文物112件(套)。其中,1号井底发现的“琅县”铭泥质灰陶罐与2号井底出土的“琅县”铭泥质灰陶片,堪称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成果。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吕雅婷介绍,在遗址的发掘中,古井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这类遗迹常因特殊的使用与废弃过程,成为古代文物的“天然保存库”。“水井作为古代先民取水、洗涤的核心生活设施,在使用阶段,取水时失手掉落的陶罐、随身工具等物品,会沉入井底淤泥,得益于淤泥的缺氧环境,这些物品能避开氧化侵蚀得以留存。”吕雅婷进一步解释,当井因干涸、淤塞等原因废弃后,又常被居民当作“生活垃圾坑”,破损的陶碗、瓷器及各类旧物被倒入其中,逐渐形成“生活垃圾层”,无意中封存了不同时代的生活遗存,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素材。
在1号井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首先清理出大量建筑用瓦片堆积,包含素面、绳纹板瓦与筒瓦等品类。待瓦片清理完毕后,一件泥质灰陶罐得以显露。考古队员在后续观察中发现,该陶罐外壁近底处印有“琅县”铭文,这一发现立即引发重点关注。随后,队员在2号井底又发现一件“琅县”铭泥质灰陶片。经比对,其铭文位置、字形与1号井出土陶罐的铭文基本一致。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很多陶片、瓦片,大约有一百余箱,带有‘琅县’铭文的只有这两件。”吕雅婷说。值得注意的是,考古队员在水井旁还发现一处手工作坊遗迹。结合“琅县”铭文的官方属性,考古队员推测两件带有“琅县”铭文的陶器可能与该手工作坊相关,且该作坊或为官营。
而从现场发掘情况看,结合发掘区所在位置,考古队推测发掘区位于战国秦汉时期琅琊邑城东南部。发掘区东侧,地势较高,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区;发掘区西侧,因地势低矮,长期有流水或积水,故被辟为手工业生产区。发掘区位置特殊,年代跨战国——秦汉这一剧烈转变的历史时期,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琅琊邑的更迭延续、文化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吕雅婷介绍,此次在陶器上发现的“琅县”铭为半通印戳印而成,未发现边框和界栏,字体为小篆,字形特征与已知秦玺印文字一致。半通印为秦汉时期官署印之一种,印章形制亦见于以往发现的秦玺印。见于著录而与琅琊有关的玺印类文物,秦玺印有“琅左盐丞”,秦汉封泥有“琅琊司马”“琅琊司空”“琅琊司丞”“琅琊左盐”“琅琊都水”“琅琊水丞”“琅琊侯印”“琅琊县丞”等。据《汉书·地理志》和《汉书补注》等记载,考古队员认为,此次发现的“琅县”戳印铭,应为“琅琊县”的省称。
吕雅婷表示,“琅县”铭文的发现,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证实秦琅琊郡县建制的官方玺印类文物,印证了文献记载,并与琅琊台遗址发现的秦代高等级建筑群、窑址等遗存共同见证了秦王朝在琅琊地区设置郡县,巡狩东方,进而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
秦始皇为何如此青睐琅琊
带有“琅县”铭文陶器的出土,不仅是《史记》中“秦置琅琊郡”的实物注脚,更藏着秦始皇要在这片黄海之滨设郡立县的深层考量。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全面大力推行郡县制改革,置琅琊郡为三十六郡之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面临着巩固政权的严峻挑战。”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涛认为,虽然秦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原六国地区的旧贵族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对秦朝的统治心怀不满,伺机而动。特别是在齐地,由于不战而降,虽然灭国,却保存了相对完整的军事与社会结构。
原齐国贵族和百姓起初虽对秦朝的统一未流血感到庆幸,但很快就发现自身利益受损。被许诺受赐五百里封邑的齐王建最终被活活饿死在边远荒野,新法令的推行也让原来的富豪、贵族失去了早先的特权。这些不满情绪在民间逐渐积累,成为秦朝统治的不稳定因素,为了加强对齐地的治理,设立郡县势在必行。
秦始皇通过多次巡游,尤其是对齐鲁地区的频繁巡视,来展示秦朝的强大国力和皇帝的威严,以此达到震慑地方、安抚民心的目的。他在巡游过程中,带领大批官员和随从,声势浩大,所到之处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和政治活动。他在琅琊台留下的刻石,由大臣李斯书写,记录了统一全国的丰功伟绩。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向天下人宣示皇权,表明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天下若是一盘棋,秦始皇落子琅琊,折射出他对海洋的深层理解。尽管当时的海洋威胁主要来自海上的盗匪和一些未被完全征服的沿海势力,但秦始皇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海洋防御的重要性。琅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秦朝东部海防的重要据点,设立郡县可以加强对沿海地区的军事管控,防范海上威胁。
从更宏观的战略布局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越国便对琅琊苦心经营。这里是联系海岱地区与三江五湖之重要港口,琅琊虽近齐地,但水、旱两路四通八达,南通海道可达吴、越,西可到莒,西北可以很方便地到达齐、晋等国,还可以向南取道莒直达鲁、宋、陈、郑等中小国家。取道沂水、泗水,再经过邗沟可至吴越故地,当时为全国五大海港之一。除东临海外,琅琊西、西南及北均是群山环绕,大珠山、小珠山、铁橛山、马耳山、五莲山等成一天然屏障,南通北达,易守难攻。春秋战国之际,越王勾践甚至将国都从会稽迁往琅琊,并筑起琅琊台。《后汉书·郡国志》在琅琊国琅琊县条下注引“越绝书”云:“勾践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琅琊作为秦朝向东拓展影响力的重要前沿,秦始皇希望通过控制此地,进一步加强对东北亚地区的联系和掌控。到汉武帝时,汉朝已降服朝鲜,东北亚列岛已有几十个小国归附于汉,华夏文化由此被带入东北亚许多地方。这种战略成果或许在秦始皇三巡琅琊时就已在他的谋划之中。
彰显实力的国家工程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琊郡为其中之一,以琅琊县为治所。而对“琅琊故城”(今琅琊镇)东南方向6公里处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也为我们揭示了更多关于秦始皇在此地战略布局的线索。
近年来经考古证实,位于琅琊台遗址中心、海拔183米山顶的“大台”主体是一座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对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汇报用了“皇家建筑”一词。
吕凯介绍,这座山顶建筑基址(即“大台”)并非孤立的单体建筑,而是以高台建筑为核心构建的完整山顶建筑群。从形制上看,它呈现出层级错落的多层楼阁外观,整体风格宏伟壮丽,尽显皇家气派。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团队还在“大台”东、西两侧清理出了房间遗迹,以及配套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这些细节充分展现了该建筑群在规划设计上的严谨性与实用性。此外,院落门址、夯土墙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进一步完善了人们对这座皇家建筑群整体布局的认知。
在遗物层面,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与建筑相关的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瓦当、铺地砖以及用于屋脊装饰的构件等。其中,两件遗物的发现尤为关键,为确定遗址的年代与等级提供了直接证据。
第一件是大型夔纹瓦当,其体量极为庞大,最大的一件直径接近80厘米。这种规格的夔纹瓦当并非首次发现,此前在秦代的诸多重要遗址中均有出土,如秦始皇陵、陕西栎阳城遗址以及辽宁绥中姜女石秦汉行宫遗址,这些遗址均与秦始皇的统治活动密切相关,进一步印证了琅琊台遗址的皇家背景。
第二件重要遗物是带有龙纹装饰的踏步空心砖。吕凯在接受采访时透露,龙纹踏步空心砖的发现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此前的秦代考古工作中,在秦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有过类似发现,而琅琊台遗址出土的龙纹砖,其图案与秦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所出龙纹砖高度相似,时代特征十分鲜明。基于这一相似性,考古团队明确指出:“我们认为这就是秦始皇时期大型工程上所用到的纹饰。”
对于琅琊台遗址的历史定位,学术界也给出一致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刘瑞认为,“琅琊台遗址应是国家工程,是为统一国家而建设的建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琅琊台遗址代表了当时的国家文化,修建琅琊台遗址是一种国家行为”。
遥想当年,秦始皇为了夯筑琅琊台,从他地迁来3万户百姓到琅琊台下居住,免除他们12年的赋税徭役,不难想象当年筑台的工程何等浩大。站在夯土层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2000多年前督造琅琊台时从四面八方征来的劳役车推、肩扛、背驮的筑台场面,他们的汗水、智慧、血泪,甚至是生命被夯进了这巍巍的高台中。
据说,当年琅琊台周围的土都被挖到山上夯台,所以海水渐渐倒灌进来,一度将琅琊台围成孤岛,琅琊台下的村民在涨潮时都要靠摆渡进出。
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不仅展示了秦始皇的雄心壮志,也反映出琅琊在秦朝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秦始皇可能将琅琊台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象征,以此来加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经略海疆的利益诉求
琅琊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控扼陆地,更在于通达海洋。
琅琊台在秦汉时期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重要节点,是帝国实施海洋战略的关键所在,秦始皇深知这一点。李涛介绍,琅琊地区在先秦时就有较为发达的经济,尤其是商业和手工业。其发达的海上贸易,使其与周边地区乃至海外都有广泛的经济往来。秦始皇在琅琊设郡县,有利于统一管理经济,推行秦朝的经济政策。
秦朝统一度量衡和货币,这一政策在琅琊地区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齐郡、琅琊郡的度量衡、货币的统一化改革,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消除了原齐国地区经济交流的障碍,使得商品流通更加顺畅,加强了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具有引领全国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另外,琅琊是优良的海港。《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琅琊郡下有“长广、不其、即墨”等县临海,琅琊港在春秋时期已是重要港口。“近年来,在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与海上活动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包括可能用于停泊船只的设施痕迹,以及与沿海其他地区文化特征相似的陶器,为理解统一帝国的疆域观提供了新证据。”李涛说。
秦始皇东巡时,与随行权臣“与议于海上”,发布阐述国体与政体的文告。这一举动可以理解为秦始皇站在“并一海内”“天下和平”的政治成功的基点上,宣示超越“古之五帝三王”的“功德”,也可以理解为面对海上未知世界所发表的政治文化宣言。这种在文化上的宣示和交流,体现了秦始皇对文化融合的重视。
琅琊,亦是秦始皇个人抱负与精神追求的投射之地。从嬴秦族来源于东夷地区的嬴汶水流域,到不断向东开疆拓土,秦始皇有一个面朝东方大海的梦。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个人性格和抱负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影响。他渴望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实现天下一统,让自己的功绩永载史册。琅琊在他眼中,是一个能够展示其统治成就和帝国威严的地方。他在琅琊停留时间较长,修建了琅琊台及行宫。这些举措都表明他对琅琊的重视,也体现了他个人的雄心壮志。
在齐地“八主祭祀”信仰体系中,“四时主”是主宰四季和农业丰收的神灵。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琅琊为齐地八神之一四时主之所在。据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学者刘宗迪分析,《山海经·大荒经》中所载大荒版图东南隅海岸线,即胶东半岛东南琅琊台一带山、海景观。羲和“浴日于甘渊”“生十日”的天文神话与琅琊“四时主”,皆与观测日出方位以定四时成岁有关;“大言之山”为大荒世界的冬至点,正与琅琊“四时主”为“岁之所始”相合;“天台高山”,其名“天台”,暗示其为仰观天象之高台,当即琅琊台;“大人之堂”和“犁灵之尸”,所呈现的为新岁之始大角星和天田星初升时在琅琊台上所举行的观星活动与农神祭祀景象;“盖犹之山”,为天台高山之外海中的一个海岛,与琅琊台相去不远,“盖犹”之名与“句游”“句榆”“根余”相近,皆为灵山岛古名。
秦始皇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深受传统信仰观念的影响,他认为祭祀神灵可以祈求国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多次来到琅琊,参与祭祀活动,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此外,统一后秦始皇极端迷恋长生之术,琅琊郡因其优越的海洋地理环境,成为他寻求长生的核心基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时年40岁的秦始皇率众臣向东巡,先是封禅泰山,然后东游至琅琊,非常喜欢,在此停留3月之久。齐人徐福上书言海中三神山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秦始皇后两次巡行琅琊,亦主要与此有关。大量征调童男女、船工、物资,这些大规模的海上求仙活动,需要地方行政机构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琅琊郡郡守及属官必然深度参与了徐福船队入海求仙的组织工作。
综而论之,秦始皇设置琅琊郡,是秦帝国在消灭齐国后巩固东方统治的核心战略部署。它既是弹压齐地、推行秦法的军政堡垒;又是控扼富庶海疆、保障海防、管理港口航运的经济与海防重镇;更是秦始皇本人追求长生不老、强化神权统治的东方基地与组织中心。
琅琊,由此超越普通郡县,成为秦帝国经略东方、沟通海陆、融合天地的战略支点。“琅琊”一词,在不断迁移中,被赋予多层文化意义。而“琅县”铭文的出土,正如一声来自地下的回响,让我们得以触摸那段雄浑壮阔的历史脉搏。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这片古老的土地或将揭示更多关于秦帝国治理智慧与海洋意识的秘密。而我们,亦将在陶片与夯土之间,重新认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伟大时代。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龙纹踏步空心砖局部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秦代石构件
1 条记录 1/1 页